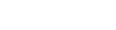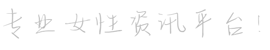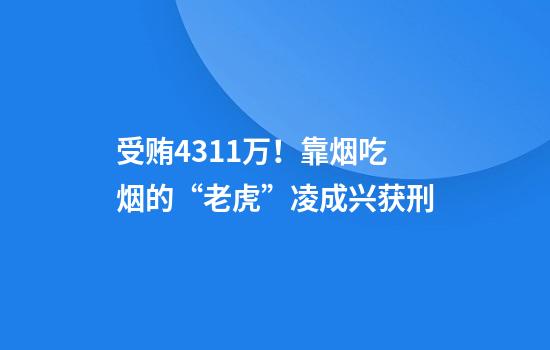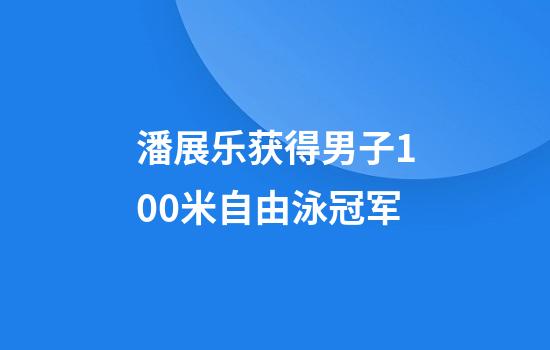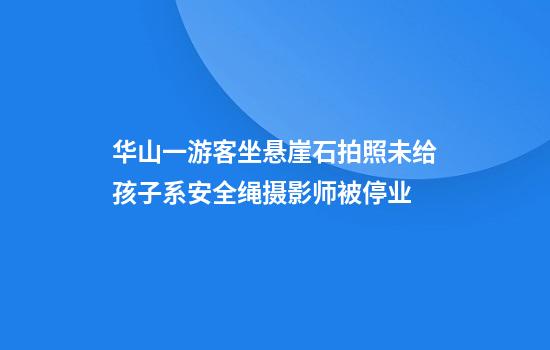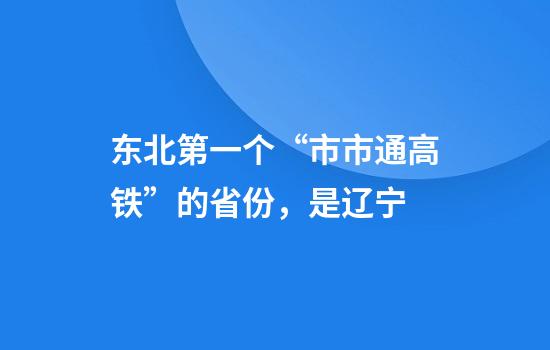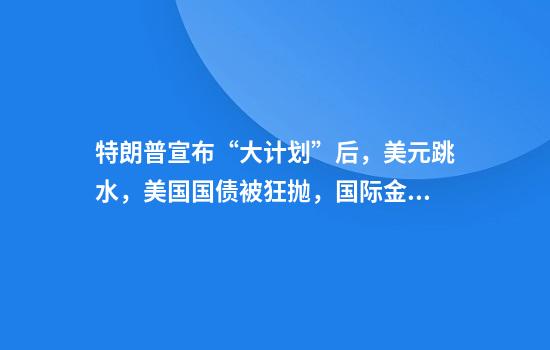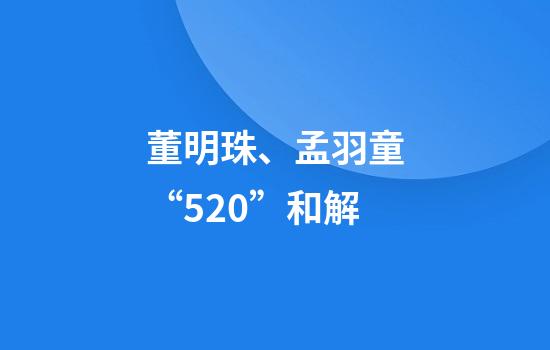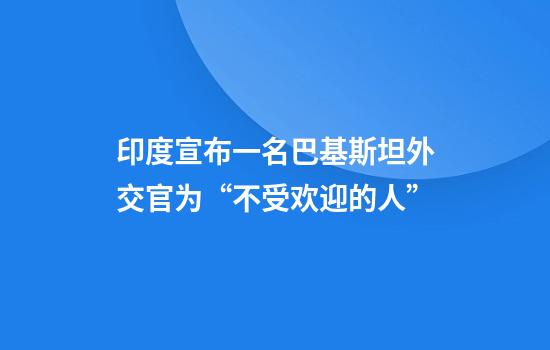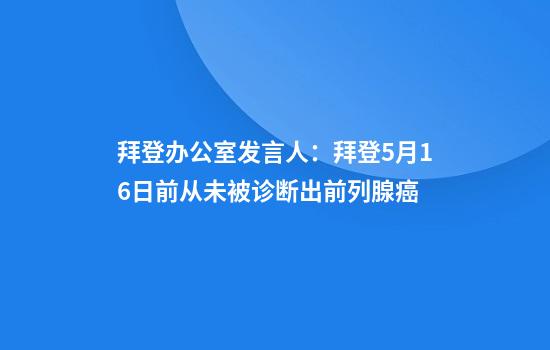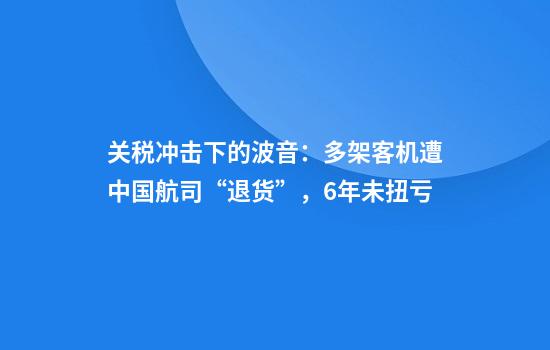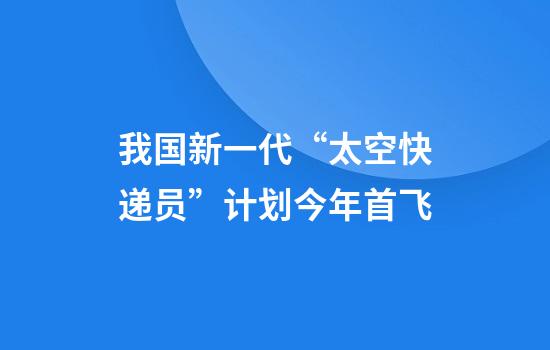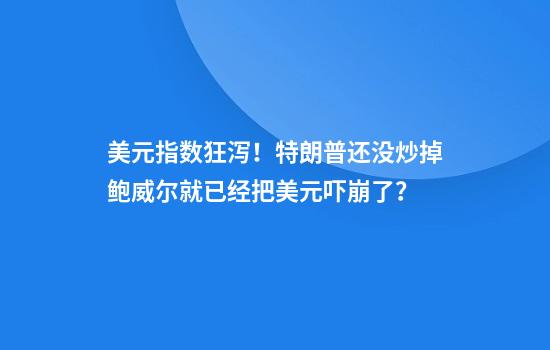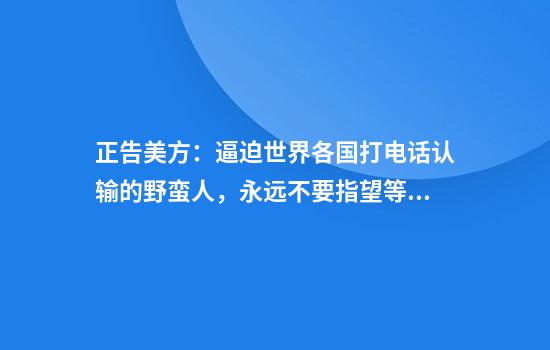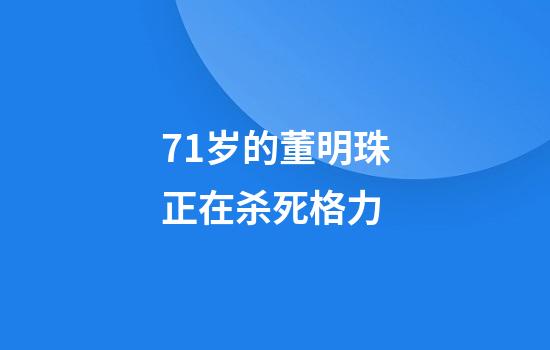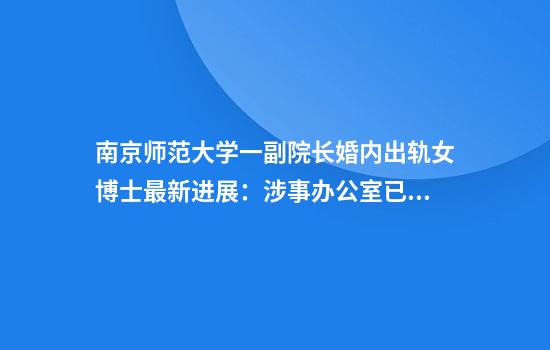记者/计巍
编辑/宋建华

在周雨涵的作品《dressing》中,女孩仿佛被食物操控的木偶,与食物矛盾病态的关系,是进食障碍人群生活中每天面临的痛苦(图|周雨涵)
开始时,它看上去只是一场和"吃"有关的战斗。
"我应该变得瘦一些,这会让我更自信,衣服上身更好看,也更能获得人们的好感。"——起初,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好,你有一个要变得更好的愿望、一个明确的目标,甚至还有着强大的意志力,节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你开始严格控制进食。体重秤上的数字几乎每天都在下降,那种实现目标的掌控感让你感觉很棒。就像一个短跑运动员想要不断地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一样,你更加自律地去"训练"自己,让秤上的数字越来越"好",而且永远可以更"好"。
饥饿被逐渐"适应",在可以吃的食物名单上,甚至只剩下了一颗苹果。大脑被训练出了一套完美的"监工模式",这不仅仅关乎体重的持续降低,更关乎你逐渐增强的掌控感和价值感。
直到有一天,掌控变成失控。
你开始被自己训练出来的那个"监工模式"反噬。它让你意识不到风险,哪怕你已经瘦到28公斤,哪怕你已经被送进ICU,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它仍要求你听它的,继续节食,否则你此前的努力就白费了,你会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事无成的失败者。
运气好的话,你会通过一些渠道早一点知道自己患上了一种叫做进食障碍的疾病——也会知道除了神经性厌食,它还可能表现为神经性贪食和暴食障碍等类型——你会去认识它,和它周旋,找机会从它的嘴巴里逃脱。但也有可能,你仍在被它控制,感到它正在一点一点"吃"掉你。
进食障碍是指以进食行为异常,对食物和体重、体型的过度关注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综合征,是一种与心理因素相关的生理障碍。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进食障碍是主要发生于青少年和成年早期女性的心理生理疾病,是精神科中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
来自精神卫生机构的数据显示,进食障碍的患病率在我国存在逐年上升的趋势。
作为多年进食障碍的亲历者,以及国内首个进食障碍同辈支持组织ED Healer的团队伙伴,张沁文和她的同伴们知道,那种被疾病吃掉的过程像是走进一条漫长又黑暗的隧道。你孤立无援,失去的不仅仅是体重、健康、感知,还有周围的一切:家人、朋友,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常常会觉得自己永远都不能从这条隧道里走出。
与吃的战斗,最终会演变成与自己的对抗——她们要去反抗那套自己训练出来的"监工模式",反抗它的评判与打压,要与自己的决心、动力、完美主义和强迫特质作斗争,而这些原本是她们身上很有力量的部分。

张沁文在给上海一所中学心理社团的学生们做关于进食障碍的分享(图|计巍)
就那样发生了
"我自己曾经有过6年的进食障碍,当时是神经性厌食症。我那个时候瘦到28公斤,(虽然)生病很严重,但我有一年半的时间,到各个三甲医院去看,都没有得到答案。"
与以往做关于进食障碍演讲不同,张沁文这次面对的是一群高中生——上海一所中学心理社团的学生们。
在做进食障碍科普博主的这些年里,张沁文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高中生。相关研究也指出,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首发的高峰年龄在15至25岁之间。
"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这两个时期是进食障碍最容易发生的阶段,因为生活可能会有剧变,比如学业压力和人际关系的变化。"徐婉清说。作为ED Healer的联合创始人,徐婉清毕业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是国际进食障碍学会委员会成员,以及哈佛青少年进食障碍预防组织委员。
徐婉清在高中时期出现过身材焦虑,这种焦虑会让她放大自己偏胖的身材,认为自己"胖得不该被同学们看到",还会让她怀疑自己一切事情都做不好,比如明明成绩还不错,却认为自己什么都学不好,甚至连学校的活动都没有资格去参加。
"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些身材非常纤细,又非常自律的博主或者明星的照片和视频,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好像需要跟她们一样才能得到更多认可,被更多人喜欢。"张沁文继续着自己的分享,"但那些有时候并不是真实的,可能经过修饰,所以我们不要拿别人最高光或者是假的一部分来评判日常生活中真实的自己。"
很多时候,神经性厌食症的"前身"有关身材焦虑——当你开始用外界的标准来评判自己,并将它内化为自己的标准时。它的发生通常在不知不觉中,有时甚至是隐匿的。除了"以瘦为美"的社会审美标准的流行,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也会交织引燃这个焦虑。
张沁文记得,她对身材的在意可能跟初中时有同学模仿她走路姿势,说她小腿粗有关。她还发现,在就读的私立中学里,当你够瘦、够漂亮,往往就能得到更多关注,生活似乎也能更加顺利。这些都在她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对于进食障碍的亲历者而言,每个人心里的那颗种子都不同。
家人对身材的评价也可能会触发身材焦虑。"小学时,我有一点微胖,爸爸会开玩笑说你得去减肥,去看亲戚时他们也会随意评价我的外貌,所以我就想我可能需要减肥了。"今年即将高中毕业的Lucy说,小学时,她就开始喝一种减肥饮料。

ED Healer曾在高中校园里做的关于身材焦虑的镜子(图|张沁文)
压力与迷茫也是风险因素。高二时因为文理分班,乔敏来到了一个成绩靠前的文科班。原本的朋友都不在这个班上。周围的人都很努力,自己也很努力,但成绩总不太如愿。
"看到那些明星那么瘦那么好看,我就开始减肥,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变成这个样子。"乔敏说,她发现只要一控制饮食体重秤上的数字就会往下掉,这种成就感促使她更加在节食上去努力,"我好像把身材和成功挂钩了"。不到一年,乔敏瘦了40斤。
很多时候,进食障碍的发生也是很多颗种子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说,性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有执念的人,吃东西、时间、学业都会管得很紧,包括运动也是,要足够优秀,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完美。"张沁文说。
当周雨涵想在考入大学后的迷茫期里找到"锚点"来锚定自己时,控制体重这件事也"趁虚而入"。周雨涵学的是艺术专业,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学习"的高中阶段进入鼓励自我发展的大学后,她找不到自己在专业上落脚的方向。即便她在大学里的成绩非常好,拿了国家奖学金,她的价值感还是很低。
在周雨涵的心中,妈妈是一个很自律、很成功的人,这似乎也成为了她的参考标准。她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有完美主义倾向。她一边迷茫,一边又想变得更好。"我好像只能控制我每天吃的东西",除了吃得很少外,周雨涵每天还极度自律地保持高强度的运动,"一天不运动不学习,就会觉得很残酷。"
在进食障碍相关的研究中,亲历者在生活中感到"失控",往往是因为没有内在的资源来应付青春期和成年期的独立思考和行动,只能专注于能控制的东西:体重和进食。通过这种方式,神经性厌食症与正在形成的自我认同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希望生活有很强的秩序感和控制感,但我们没办法控制外部的事情,很失控,所以才想去控制自己。"周雨涵说。
真正残酷的是,这种控制也会失控。吃得很少,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让周雨涵感到身体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经常处在很紧绷的状态里,很容易焦虑和暴躁,"当你发现连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时候,你就会反过来更加责怪自己,自己的价值感会更低。"
另一重失控是,你逐渐"适应"了饥饿,从每天只吃一个苹果,到只吃几颗小番茄。这个阶段身体会发生很多变化,像是一种"预警":生理期中断、不再长高、没有体力、失眠、抑郁、焦虑、严重脱发、长出老人斑,还有人会发现汗毛变多了,那或许是因为身体要保暖。
但进食障碍的亲历者们很难在这种"预警"下做出改变。
28公斤,这是张沁文2018年3月被送入ICU急救时的体重。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上面写着:多脏器功能损伤。在这张粉红色的纸上,她的痛苦也终于有了名字——厌食症。而此前,父母曾带着正在读大学的她辗转各种科室就诊:内分泌科、妇科、消化内科,但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准确地告诉她到底是怎么了。
她被抢救了回来。《中国进食障碍防治指南》中指出,神经性厌食的死亡率高达5%~15%,在所有心理障碍中死亡率最高。但神经性厌食并没有在这里和她"断绝关系",她甚至会用手机软件继续去计算一个药丸上糖衣的热量。
她的大脑已经被"训练"出来了一套强硬的"监工模式","我知道自己很瘦,不应该再瘦下去,但我开始害怕进食这个行为本身,它在颠覆我之前的自律。"这个"监工"会告诉你:吃就意味着你彻彻底底失败了,你无法掌控你自己的人生,甚至是任何事情。
出院回家一个月后,张沁文住院时增长到39公斤的体重又迅速掉了5公斤。

神经性厌食症导致张沁文一度瘦到28公斤(图|张沁文)
对抗:谁吃掉谁?
"我拼尽所有力气去和脑子里那个斤斤计较的小黑人作斗争,但它依旧控制着我。"张沁文试图去讲述她为什么没有办法停止节食。
这个"小黑人"是谁?它从哪里来的呢?
她给出的答案是:我一直在不知情地"虐待"(控制)我的大脑,直到有一天大脑习惯了这个模式——那个"小黑人"出现了,也就是那个"监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都在帮助张沁文成功地掌控自己,告诉她要继续努力,要在控制体重这条路上做到完美,告诉她哪怕吃掉两块饼干或者喝上一杯牛奶,就是失败和软弱的表现,是会被嘲笑的。
为了"更好",她一直跟随着"小黑人",直到它把她引向深渊。想要从这个深渊里逃出来困难重重。在她看来,这是对大脑的又一次"虐待","当它习惯了那个(节食)模式,我又要进去告诉它这是不对的"。张沁文觉得自己像是在两个灵魂间游走、挣扎,这让她一度想要轻生。
2018年,从ICU里出来半年后,因为太过虚弱,张沁文在骑自行车时突然感到眩晕,连人带车摔倒。醒来时,她已经被送到了医院,头上裂开了一个口子。由于太瘦了,医生在她脑袋上缝针的时候不敢打麻药,她就硬扛了下来。
处理完伤口,和妈妈从医院走出来时,一阵夏夜晚风吹来——她看见上海街边店铺里五颜六色的灯光,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这么久以来,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爱过自己,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感受。她转头跟妈妈说:我想吃一碗大馄饨。这可能是那几年来,她第一次说想吃一样东西,而且它的热量还不低。
张沁文在很多演讲中提到过这个发生改变的"重要时刻"。这阵"夏夜晚风"究竟吹散了什么,又让什么得以显现?她说,街边的那些餐厅是她小时候经常和朋友们去的,那时的她开朗活泼。生病的这些年,她已经离开这样的烟火气很久了。因为对进食的严格控制,她经常一个人待着,也不敢走进这些店。
她还感受到,20岁之前一直都在依靠外界的标准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足够好,用"虐待"自己的方式去达成很多看起来完美的事情。
"那一刻,我觉得我应该在餐厅里,我应该去享受那些灯光。"张沁文说。
她开始尝试吃东西了。这是神经性厌食症康复的第一步,虽然那个"小黑人"还在。
2019年,张沁文拍摄了一部有关自己患神经性厌食症的短片,并发布到社交媒体。大量的评论和私信,让她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年轻女孩有着与她极其相似的、隐秘的经历。很多人和一年前的她一样,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相似的痛苦,有人甚至经历了十几、二十几年。她开始在网上不断地去分享进食障碍的科普信息。
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张沁文独自来到英国留学。
新的问题也追了过来。因为孤独,她开始出现不可控的大量进食。严重时,她会半夜起床吃冰箱里的冷冻披萨,生存的动力就是寻找下一个能果腹的食物,不管是番茄酱、花生酱、带血的牛排,还是猫粮。吃,变成她在无助和压力下的唯一抓手。
很多进食障碍的亲历者都会谈到,这种暴食很像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极度缺乏营养的身体需要快速地摄入很多能量。虽然它像是去制衡"小黑人"的对手,但是它也是不可控的。在暴食之后,她们会受到"小黑人"的攻击,有些人会给自己催吐。这会让她们陷入另一重黑暗循环中。
牛津科普系列《进食障碍》一书中指出,大约50%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成人经常有暴食和/或清除行为,这种清除行为是指为了清理掉吃下的食物而做出的包括催吐在内的一些行为。
"非常大的失控感,在吃和学习之间来回徘徊,后来就演变成,你只要碰到学习上有瓶颈,就会通过进食来解决。"到了高三下半年,乔敏也开始出现暴食,"吃完后又会自责,但是下一次还是会这样。"
刚到英国时,张沁文还很瘦,但短时间内猛烈地暴食让她的肚子快速变大,甚至有点呼吸不畅,但同时又肋骨分明。由于对食物无法抑制的依赖,她的生活再次失控了。
2019年5月,张沁文坐上了回上海的飞机。在飞机上她吃了很多抗抑郁的药——其实半片药就可以让她很快睡着。她害怕明天的出现,"这好像是我那么多年最恐惧的一件事,它(暴食)会不断地发生,明天还会继续这样"。
回国后大概半年,张沁文的体重极速增加到70公斤。她把自己关在家里点外卖,从早吃到晚,"不吃就过不了下一秒"。她感到自己每天都在膨胀,像做梦一样。但同时,她也在试图给自己找事情做,比如说,继续通过社交媒体去做进食障碍的科普,画画,去公共艺术公司上班。
一些变化在发生。她很想要表达,画了很多宣泄的画。她一面感受到坏情绪如同狂风暴雨一样来袭,另一面又很想要生存。作为科普博主,她收到了很多人的鼓励,很容易哭。她说自己"充满激情地"去做很多科普视频,"很热烈地"讲述以前的经历,也"很热烈地"地去鼓励别人。而在此前的厌食期间,她没有任何感受、麻木,甚至连死都不怕。
她萌生了给进食障碍群体做艺术展的想法。她想去反抗"女生需要更加苗条"的声音,想让更多人知道大环境中那些不友善的地方,她想用"一个很大的声量"让大家知道这些。

张沁文用跑步机做的关于"运动强迫"的作品(图|张沁文)
2019年,张沁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进食障碍艺术展的共创招募,希望能收集一些跟进食障碍相关的物品。正在读高一的张至瑜看到这个招募贴,当时的她正在经历进食障碍。
张至瑜联系上张沁文,告诉她自己要送给展览一台跑步机。这台跑步机的背后是张至瑜的运动焦虑。张沁文用它做了一个关于"运动强迫"的作品——跑步机上放着许多双跑烂的鞋子。"运动强迫"是许多神经性厌食患者会有的特点,张沁文自己也经历过,在她瘦得已经皮包骨的时候。
还有人给这次展览寄来一叠外卖单和一封信。信里说,在和朋友们出去吃完饭之后,她还会在宿舍里点外卖暴食,吃完再去催吐,这些就是她点外卖的记录。展览的创作者们把这些外卖单剪贴成了大家手牵手模样的作品。
乔敏也是在这时认识张沁文的。很多进食障碍的亲历者在了解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之前,都像一座孤岛,乔敏也一样。她通过张沁文的纪录片和科普视频了解到自己的情况是进食障碍,"她经历的我也都经历过"。
在和张沁文交流时,她发现暴食问题那时还在纠缠着张沁文——"我们(电话)聊了差不多十分钟,她说我不跟你聊了,我的外卖到了"。乔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进食障碍的人脑子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吃,所有的事情都要放在吃后面。"
"它会一直反反复复折磨你,把你的意志都快磨没了,磨得你没有心气儿去改变。"乔敏说。那时,她正在读大学,或许是因为远离了高中时的压力,她的进食障碍有了好转,但她知道张沁文正在经历什么,"你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但又看不到尽头"。
张沁文一直记得在自己最黑暗的那个时期,乔敏在电话里给她的那句鼓励:"现在就像在隧道里一样,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在隧道那一头等你,你一定会出来的。"

2024年,张沁文正在布展(图|张沁文)
隧道那一头
张沁文给这个展览设计了一条动线:从一个人一开始受到外界的影响,想自律节食,到后来行为举止发生了改变,影响到心理状态,再到如何走出来。
事实上,这个展览也是张沁文从进食障碍中走出来的助推剂。因为她发现,自己摊上了一件需要消耗她很大精力的事。展览陆陆续续准备了2年的时间,几次差点夭折。她没有经验,在这之前很少有人做过关于进食障碍的策展,她要快速学习,做出决策,要带40多人的团队,也背负着很多期望。
她能感受到自己身上"强迫""执念""要强"的特质在办展这件事情上的作用力——"我特别想办成这个展览",在很多做不下去的时候,她的抵抗心理很强烈,"我想完成它"。而这些特质原本是促使她患上进食障碍的"种子"。
"我那个时候开始有新的衡量和选择了,比如说我会想,我今天是暴饮暴食,还是把这个展览再优化一遍。"张沁文说。
相关研究者也指出,与进食障碍的斗争里,要解决的不是把亲历者身上的珍贵品质从他的身上拿走,而是把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进食障碍者"的能力转向更健康的努力上。
2021年5月,这个国内首个关于身材焦虑的艺术展开幕。现场有很多"奇怪"的作品,比如说,一个被关在鸟笼里的提线木偶被许多红线束缚着,坐在摆放着蛋糕的餐桌前,它被一个破损的大脑控制着,手中握着尺子和刀;五彩斑斓的手臂从冰箱里涌出来,下面是一张女孩的照片,她被所有手臂围绕着,只露出眼睛。
周雨涵也是在看到这次展览后,发现原来进食障碍的困扰还可以通过艺术表达出来。她开始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在她的一组摄影结合版绘的作品里,一个眼神很无辜、穿着公主裙、摆着像玩偶一样姿势的女孩,裙摆上是大量食物油渍,背景是堆积如山的食物。这个作品对于周雨涵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终于找到了一种"语言"去表达自己的状态。
在这之前她很难坦然地去讲述这些,她像是被困在了一种"假象"里,充满了孤独与自我否定。"互联网带有很大的滤镜",这让她觉得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光鲜亮丽,就像她自己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成绩很好、很自律,也很正能量的人,"但其实很多人背后都有难以启齿的一些混乱、一些失控、一些焦虑,对我来说就是食物"。
做完这幅作品之后,周雨涵看到的是:这个女孩——她自己,在向她求助。
她告诉女孩:"没关系,这些都是可以去接受的。"
张至瑜在国外读大学时,把进食障碍放进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论文里,"它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身材焦虑?东亚社会对于女性‘白幼瘦’的审美是怎么出现的?这背后不仅仅是男性,还包括卖减肥药的公司、整形公司,它们为了赚钱一直在引领这样的潮流,还有媒体的影响。"
对于张至瑜而言,学术研究让她有机会去"解构"进食障碍,把它从一个令人痛苦的疾病转换成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或许总会有一个时刻,你可以有机会从那个"小黑人"的魔爪里抽离出来。比如说,从张沁文身上吹过的那阵夏夜晚风,周雨涵看到的这个正在向她求助的女孩,或者张至瑜的学术研究。对于石玙睿而言,这个时刻来自《一个苹果们》。
《一个苹果们》是石玙睿的本科设计专业的毕业作品。2022年,正在准备毕业作品的她,处于进食障碍很严重的阶段,甚至每天只吃一个苹果。那时,她通过看张沁文及其他博主的科普视频知道自己生病了,也知道了一些恢复的方法,但每一种方法都需要开始吃东西,但她"不敢吃",也不知道恢复到什么程度是"正常"的。
她决定把毕业作品的主题放在这件让她痛苦的事情上,从访谈进食障碍人群开始。
石玙睿访谈了三十多个进食障碍者,其中有社会底层的人,也有出身高知家庭学历很高的人,她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原因和经历。那阵子,每天从实习的设计工作室下班后,晚上八点回到学校,她就开始一到两个小时的访谈。"你要去接收很多情绪,去共情,"石玙睿说,而她自己当时还处在很糟糕的状态里——厌食与暴食的交替出现。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当她不得不把这些时间放在具体的人和事情上时,她每天思考的问题不再是"我今天吃了什么",也不用每天花几个小时去"选外卖"——是吃"低卡"的食物,还是"好好吃饭"?她还发现,当她在访谈中把那些与进食障碍有关的专业名词重复说过很多遍之后,自己有了一个"抽离的形象",这让她觉得,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说也不丢人,这只是一个医学上的专业概念。
访谈期间,有一个晚上,石玙睿把此前收集到的所有关于进食障碍的资料,打包发给了自己的父母和朋友,她希望他们了解这种疾病,并且告诉他们自己能够搞定。而在这之前,她没有向任何人主动提起过自己的情况,很多时候甚至是回避的,比如说她害怕和妈妈一起吃饭,因为妈妈也在因为这件事而感到崩溃,她还会跟好朋友声明:我不会跟你一起吃饭。但实际上,对于这些,她都心存愧疚。
原本准备好去面对一场"狂风暴雨",但石玙睿转天收到的却是:没关系,你自己搞定就好,有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她说自己醒来看到这些消息后"暴哭":"我好像把进食障碍这个事情看得太天大的重要了。"
石玙睿开始尝试去和身边的人"真实相处",而在生病的这些年里,她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自己玩"。当把注意力放在身边的人身上,她发现朋友中很多人也在减肥,也会多吃一顿或者少吃一顿,这原来是很正常的,是不用去责怪自己的。

石玙睿的作品《一个苹果们》(图|石玙睿)
《一个苹果们》这个作品最终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现,里面集合了石玙睿对30位进食障碍患者的对话。在毕业答辩展示后,有老师问她:你当时为什么不吃饭?吃饭有这么难吗?如果是以前,石玙睿可能会扯个别的话题,但这次,她直视了这个问题,很认真地解释什么是进食障碍,因为在做访谈的过程中,她发现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我觉得这是需要严肃去重视的东西"。
"大家需要一个环境的支持。"石玙睿说,这种支持包括身边人、共同经历人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持。
五年前,张沁文和同伴们创立了进食障碍同辈支持组织ED(Eating disorders) Healer,团队有二十多人,有进食障碍的亲历者,也有关心这一疾病的人。石玙睿、周雨涵、张至瑜、乔敏都是ED Healer的伙伴。在做进食障碍科普的同时,ED Healer也试图做一些事情帮助进食障碍的预防,如走进大学、高中校园做讲座,开办工作坊,策划展览等。
2024年,石玙睿的《一个苹果们》展出在ED Healer参与策划的名为"爱,食物与生命"的进食障碍科普艺术展中。周雨涵的作品也出现在这里。展览的场所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600号画廊,这所医院曾在2017年成立国内首个进食障碍诊治中心。
据相关数据统计,2017年,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门诊人数为1599例,到2021年,门诊人数增长为4281例。此外,进食障碍患者年龄总体有低龄化趋势,尤其在致死率最高的神经性厌食患者低龄化趋势更为明显,2022年,未成年人在神经性厌食患者中占比77.6%。
在青少年中,厌食症的治愈率在50%~70%,成年人厌食症治愈率则是45%~50%。贪食症治愈率更高一些为70%,暴食症则为75%。
现在的她们康复了吗?
在张沁文看来,进食障碍的康复是个渐进的过程,从厌食到开始吃东西,经历暴食,再过渡到正常饮食。康复也是多维度的,包括身体、心理、认知、社交、做事风格等方面的康复,这跟进食障碍成因一样,也是相互作用的。
在做完2021年的身材焦虑展览后,张沁文身上的那种强烈对抗的能量开始逐渐平息。这其中也包含她理念上的变化,例如,从"身材积极"到"身材中立"。"在刚开始时,我可能会说,大家其实什么状态都是美的,所以你要有足够的自信。"张沁文知道,作为一个科普博主,这种表达是特别的、吸引人的,她曾经也相信这个力量。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她对自己有着过高的期待,比如说,作为康复者的自己不能复发,每天必须很积极乐观等。直到她发现这种超级用力的"积极"也可能是存在泡沫的、"有毒"的,像是一种补偿。"就像厌食和暴食一样,一定是平衡的状态才是对的。"
寻找这种平衡或者说是"中间状态"需要大量的耐心和实践。在张沁文看来,它是减肥也可以,不减也可以,自己的开心和舒服最重要;是不再只接受单一标准,而原本在她看来100分以外的就都是0分;是可以接受自己不喜欢运动这件事,尤其是那些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然后去尝试自己喜欢的舞蹈、游泳,因为每个人寻求健康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个"小黑人"和它的对手还在吗?
它们可能会一直埋伏在那里。
大概一个多月前,因为做新的展览时遇到各种麻烦,压力很大,张沁文有一天吃了很多东西。"我意识到自己有点过量了,是有点情绪化的。"张沁文说,当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她会尽量停下来休息,找朋友倾诉几句,可能第二天就会好。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康复并不是消灭进食障碍,而是改变和它的关系。
"我还是会睡不着,或者吃多,但是我告诉自己不把它当一回事,就像一个感冒发烧。"周雨涵说,"你的生活中不只有你自己和眼前的这些食物了,你可以去做很多事。"她也找到了自己专业的价值和意义,尝试用艺术的方式去帮助进食障碍群体。
它也会冷不丁地在乔敏的生活里冒出来,当她的负面情绪没有得到排解时。在这种偶尔的交手中,乔敏现在有一半的概率可以控制住它,如果没有,她也会接受,"我不再害怕它,或者说我允许它",就像一个正常的情绪波动。
石玙睿逐渐把进食障碍当成理解自己的契机,她会去思考自己的"来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生课题",它可能呈现为进食障碍,也可能表现为其他。这需要你自己去认识它。